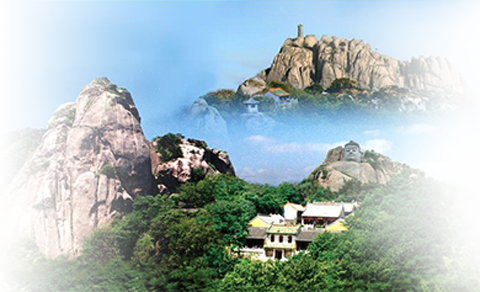《天平》2014年第7期
接近正义
——从电影《似是故人来》说起
王学文
电影《似是故人来》是一部美国好莱坞悲情电影,由享誉影坛的李察·基尔与朱迪·福斯特联袂主演,讲述了男主人公冒名顶替他人丈夫,并最终为着全镇人们的幸福而自我牺牲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南部的一个村庄——藤山,刚刚经历内战的洗劫,只剩下老弱妇孺和百废待兴的土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悄然走进村庄,熟练地叫出他所见到的每个人的名字,当有人认不出他时,他便讲出那人小时候干过的傻事。村里人惊喜地认出他就是那个六年前离家出走的大地主杰克。大家簇拥着他浩浩荡荡走向阔别多年的老房子,孀居多年的妻子劳娜,听说丈夫归来的消息急忙跑回家更衣打扮,在门口丽妆相候。
劳娜从一开始就未曾深信这个温情脉脉的男子就是从前那个粗鲁暴躁的丈夫,但归来的杰克清晰地记得那件新婚时劳娜亲手缝制的白衬衫,而他幽默的言谈与浪漫的举止也慢慢融化了劳娜冰封已久的芳心。
为了让村民脱贫致富,杰克动员村民纷纷捐物,并承诺把他的土地分给大家,提供工具和肥料,到时一半的收成归村民,一半来付他欠的抵押款,等付清抵押,他就把土地平价转让给大家,甚至包括黑奴。在劳娜的帮忙说服下,村民们先后将家里的宝贝都拿了出来,杰克用卖得的钱千里迢迢赶到弗吉尼亚买到了烟草种子,在田里大量种植烟叶。全村人鼓足干劲齐上阵,烟草的种植形势一片大好,杰克和劳娜的感情也大幅升温。
与此同时,奥林,一个拖着因内战导致褪残而安装木腿的青年牧师,对杰克却一直怀恨在心。因为多年来他一直照顾并爱慕着劳娜,而杰克的突然还家摧毁了他甜蜜的憧憬。一次偶然的机会,奥林终于发现那个男子并非真正的“杰克”,只是面貌相像,他原本是克拉克县的一名教员,曾经卷走了全村捐建新校舍的1200元钱,玩弄并遗弃了一个女人,还因为参军后开小差被北佬抓了起来,是个劣迹斑斑的惯犯,他的真名叫汤森。
当一年的耕耘终于迎来了烟草的丰收,劳娜也生下了她和杰克的小女儿,正在大家欢喜一堂的时候,厄运突然从天而降。两个黑衣联邦执法官拿着公文通知前来逮捕杰克,理由是他杀害了一个叫查尔斯·康克林的人。
劳娜为了帮忙洗脱罪名,接受了奥林提出的办法和条件,坚称这个来自藤山的男子不是真正的杰克,而这也是她一直隐隐怀疑的,因为曾经的杰克不会对妻儿那么体贴关爱,不会对村民那么友好,也不会对黑奴那么宽容。
在法庭之上,汤森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承认他不是杰克,而是一个另有其名的乡村教师和无赖,由此失去他除生命以外的全部;要么死守杰克之名,因谋杀罪而被判绞刑。为了爱情、名声以及村民的幸福,汤森选择了后者。他巧妙地斥退指称他是假杰克的证人,拿起一张跟村民签的合约,提醒劳娜,如果他不是杰克的话,这些契约都将成为废纸,村民都将会重新成为穷光蛋;如果他不是杰克的话,儿子和女儿都将成为遭人唾弃的私生子……在汤森咄咄逼人的追问下,劳娜最终含泪承认,在她心里,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丈夫。最后法官宣布:谋杀罪名成立,杰克被处以绞刑。
被拉向绞刑架后,套上绞索的汤森大声呼叫劳娜的名字,劳娜拨开人群,冲到台下,两人四目对望泪如雨下……汤森最终用他的生命帮自己和劳娜挽回了声誉,也铺就了村民的解放之途。
影片名称的中文翻译极富神韵,“似是”二字颇为传神地表现了人们的疑问,战场归来之后的杰克,与过去的他判若两人,他究竟是不是杰克?法庭审判的结果,主人公杰克的身份虽受质疑,却没有被最终戳穿。这个疑问也变得不可知,但悲剧性的结局却为影片攒足了赚人眼泪的资本。
在一个法律人眼里,任何动人心魄的故事都需要还原成最基本的法律事实。细数来看,这部电影涉及的法律问题有多个方面:首先是汤森冒用他人的姓名,侵犯他人的姓名权;继而以欺骗手段非法取得杰克的田产,侵犯其财产权;同时,汤森以杰克的名义还家,与杰克的合法妻子劳娜同居,侵犯了劳娜的性生活自由权。再看劳娜,在她内心确认“新丈夫”其实是“冒牌”之后,而在知悉其真丈夫已死之前,故意与“冒牌丈夫”发生非婚内性关系,无疑具备通奸的故意。尽管如此,电影里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和跌宕起伏的生死抉择,还是把有关理智与正义的思想成分冲得一干二净,只让观众陶醉于男主人公崇高的道德张力和美丽动人的爱情。
然而电影中的故事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取自真实的案例。在冯象的文章《木腿正义》里,同样提到过这样一个案例:在十六世纪,一个名叫马丹的巴斯克人娶妻生子后,有一天突然离家出走,一去不归。八年后,一个自称马丹的人来到巴斯克,把他叔叔从老爹那里骗来的遗产要了回来,于是,马丹的叔叔心生怨恨,认定新马丹是个骗子,并非真马丹,便将其告上法庭。在法庭上,新马丹沉着冷静,答辩自如,眼看一系列的指控都不成立时,一个木腿人闯了进来,而他就是真马丹。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指证,新马丹被判处绞刑。
这桩冒名顶替的奇案,曾吸引诸多历史学家去考证故事的真伪,也让法学家去思考争辩一个深层次问题: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孰轻孰重?运作生杀大权的司法程序,实际上有时候会“不靠谱”。因为真马丹与假马丹两副面孔无从区分,若非木腿人出人意料地闯进法院,法官很可能得出离真相十万八千里的结论。正是在千钧一发的那一刻,真正的马丹冲进了法院,才让大家寻找到了真相。
自古以来,正义,无论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还是制度设计,始终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设置司法制度的基本初衷。但实际上,在现实当中的每个案件中,正义并不会像那个拄着木腿的真马丹,每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很多时候,司法的判决也未必能保证是正确的判断,因为真相只有一个,而真马丹与假马丹却是如此迷惑人们双眼。
在中国古代,只要能够达到实体的正义,程序往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比如各个朝代的法官各显神通,或者凭借直觉、经验大胆臆测,或用兵法计谋和诈术,有时甚至借助神明来断案,而这至今深深影响人们的观念。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判中认定的事实一般是在现有证据和规则框架内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一旦由于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在适用法律上出现偏差。如何最大限度地接近“看得见”的正义,满足人们对公正司法的期待与信任呢?这就需要以理智的规则和规范的程序为前提,从程序上确保审判的过程最大程度地达到实体正义的目标,即符合正义的要求。换言之,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在司法过程中尽量做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竭尽全力让我们认定的事实尽可能接近客观真实,让裁判结果最大限度地被社会和当事人接受,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
在当今复杂万端的社会当中,不能再为追求结果而牺牲过程,正义只能是在遵循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之后被无限地接近。这,也许是木腿人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提供给我们的启示。
相信只有如此,法律才能在促成契约理性的建立中,培养人们更加自律的行为规范,涵养整个社会公共秩序的法治精神,从而促进社会法治氛围浓度的不断提升。